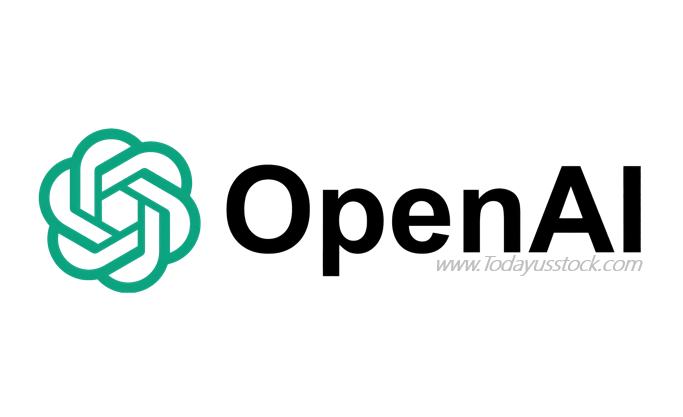小约翰·P·杰克逊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教授,他在The Conversation上的文章指出,特朗普政府的反智行动之一,就是反对科技界对种族是社会建构而非生物学的共识。

在特朗普最近一系列行政命令中,有一项警告称,关于种族的“扭曲叙事”是“受意识形态驱动而非基于真相”。这一命令点名了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当前举办的展览《权力的形状:种族与美国雕塑的故事》作为例子。这个展览呈现了跨越两个多世纪的雕塑作品,展示艺术如何形成并再现种族观念和意识形态。
这项行政命令谴责该展览“宣扬种族并非生物现实,而是社会建构”的观点,指出展览中提到“种族是人类的发明”。
行政命令似乎反对这样的观点:“尽管一个人的基因会影响其表型特征,自我认同的种族可能受到外貌影响,但种族本身是社会建构。”
但这句话并非出自史密森尼,而是来自美国人类遗传学会。科学家普遍否认种族具有生物学实质。声称种族是“生物现实”违背了现代科学认知。
我是研究种族科学史的历史学者。行政命令将“社会建构”与“生物现实”对立起来。而这两个概念的历史恰恰说明,现代科学最终得出种族是由人而非自然创造的观点。
种族确实存在,但到底是什么?
在20世纪初,科学家普遍认为人类可以根据身体特征划分为不同种族。根据这种观点,科学家可以识别群体之间的身体差异,如果这些差异可以遗传给后代,那么就能定义为一个种族“类型”。
这种“类型学”方法的结果混乱不堪。达尔文在1871年就感到很沮丧,他列出13位科学家的观点,种族数量从2个到63个不等,在接下来的六十年里继续混乱不堪。种族划分者几乎各执一词,因为没有两个科学家能就该测量哪些身体特征、如何测量达成一致。
种族分类面临的一个难题是,人类身体特征的差异非常微小,科学家难以用这些差异来划分群体。
1906年,非裔美国学者W.E.B.杜波依斯指出,“在黑人与其他种族之间划分肤色是不可能的……在所有身体特征上,黑人种族都无法自成一类。”
但科学家们仍然尝试分类。在1899年的一项人类学研究中,威廉·里普利依据头型、发质、肤色和身高对人群进行分类。1926年,哈佛人类学家、当时全球最知名的种族类型学家欧内斯特·胡顿列出了24种解剖特征,例如“颞下结节和咽隐窝是否存在”以及“尺桡骨的弯曲程度”,他还承认“这个列表当然不是详尽的”。
所有这些混乱与科学应有的运作方式背道而驰:随着研究工具的进步和测量方法的精确化,研究对象——种族——却变得愈加模糊。
当雕塑家马尔维娜·霍夫曼的《人类种族》展览于1933年在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开展时,将种族描述为一种生物现实,尽管这个概念本身难以定义。世界知名人类学家亚瑟·基思爵士为展览图录撰写了序言。
基思否定了科学是辨别种族最可靠方式的说法,他表示,一个人种族的特征“只需一眼便能识别,比一群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还要准确”。
基思的观点完美体现了当时人们的信念:种族必须是真实存在的,因为他在周围看到的就是如此,尽管科学从未能证实这一现实。
然而,在种族科学研究领域,情况即将发生改变。
从文化角度解释差异
到1933年,纳粹主义对从科学角度研究种族有迫切的需求。人类学家舍伍德·沃什本在1944年写道:“如果我们要就种族问题与纳粹展开讨论,那我们最好先搞清楚真相。”
在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初,两个新的科学思想逐渐形成。第一,科学家开始将文化而非生物作为群体差异的驱动因素。第二,群体遗传学的兴起挑战了种族作为生物现实的观念。
1943年,人类学家鲁思·本尼迪克特与吉恩·韦尔特菲什合著了一本面向大众的简短作品,同样取名为《人类种族》。他们主张,人类之间的相似性远大于差异,而这些差异源于文化和教育,而非生物因素。
随后,这一思想还被改编为动画短片,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。本尼迪克特和韦尔特菲什指出,尽管人们在身体特征上确实存在差异,但这些差异毫无意义,因为所有种族都能学习,所有人都有能力。
“文明的进步并不是某一个种族或次种族的专利。”他们写道,“当浅肤色的欧洲人还在穿兽皮、对铁一无所知时,黑人已经制造铁器、织出精致的布料。”
相较于含混不清的生物种族说,文化解释更有说服力。
这种向文化的转向,与生物学知识的一次重大变革相一致。
理解进化的工具
特奥多修斯·多布然斯基是20世纪最杰出的生物学家之一。他与其他生物学家对进化变化极为关注。所谓的种族被认为是不随时间变化的,因此在理解生物进化过程中毫无用处。
一种新工具——科学家称之为“遗传群体”的概念,更具研究价值。遗传学家多布然斯基认为,应根据一组共享基因来定义一个群体,以便研究有机体的变化。随着时间推移,自然选择会改变群体的进化方向。但如果某个群体无法帮助解释自然选择过程,遗传学家就应放弃,转而研究基于另一组共享基因的新群体。
关键在于,无论遗传学家选择哪种群体,都在不断变化,没有哪一个群体像所谓的“人类种族”那样固定不变。
舍伍德·沃什本与多布然斯基是密友,他将这些思想引入人类学。他意识到,遗传学的意义不在于将人类划分为固定群体,而在于理解人类进化的过程。这一转变推翻了他的老师胡顿所教授的一切。
1951年,沃什本写道:“没有任何理由将一个……群体划分为一系列种族类型。”
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。假设任何一个群体是固定不变的,都会阻碍对进化变化的理解。遗传群体并不“真实”,是科学家为理解有机变化而设计的工具。
理解这种根本差异的一个好方法,是类比过山车。
去过游乐园的人都见过那种写着“身高达到多少才可乘坐”的标志。但没人会因此认为这些标志划分出了“真正的高个子”或“真正的矮个子”,因为另一个过山车的标准可能会完全不同。标志只定义谁能乘坐这个特定的过山车,仅此而已。
这不是用来划分谁“真正”高的标准。
同样,遗传学家将“遗传群体”用作“推断现代人类进化史的重要工具”,或因为“在理解疾病的遗传基础方面具有重要意义”。正如试图用螺丝刀敲钉子的人会发现,工具必须用在合适的任务上,遗传群体就是为特定生物学用途而设计的工具,而不是划分种族的工具。
沃什本认为,凡是想划分人类的人,都必须提供“将我们整个物种细分的正当理由”。
史密森尼的展览展示了被种族化的雕塑是“既是压迫和统治的工具,也能成为解放与赋权的工具”。
科学界认同它的观点,即种族是人类发明的概念,而非生物现实。